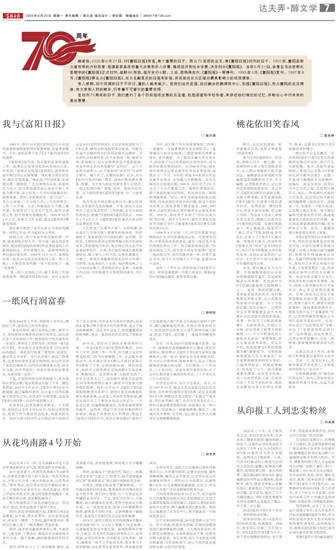□ 夏良坤
那日,办公室的老陆一脸郑重地告诉我,县里正筹备复刊《富阳报》。
复刊后的《富阳报》一经面世,便给人耳目一新之感。它将富阳的大事小情尽数收录其中,让人得以知晓家乡的点滴动态。编辑部设在影剧院对面越剧团那简陋的房子里,不少编辑、记者都是老熟人,这让我对这份报纸倍感亲切。没过多久,《富阳报》便开启创新之路,风格不断变换,尤其是增设的《周末》副刊,在读者中收获诸多好评。每周单独一期的《周末》,内容丰富有深度,很是耐人寻味。身边有人在本土报纸发表文章后,便极力怂恿我也为《富阳报》写稿。在他们的鼓动下,我心旌摇动,提笔写下“春江评论”《假如阿 Q 没有死》,还登上了《周末》头版头条。香港回归前夕,我创作的《香港正向“母亲”走来》和《回归,我们干杯》两篇散文诗在报纸发表,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,文中的不少语句还被中学生摘抄进作文里。
后来,报社搬迁至天马大厦。尽管编辑部前后办公室间的通道狭窄逼仄,但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。我也成为当时《话题》版面的主要撰稿人之一。每周一期的话题文章,常常能看到我的名字,有时整版都是我的文章,这让我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为了寻找新话题,我绞尽脑汁。记得民营企业家蒋敏德走进中央电视台为抗洪救灾捐款的现场,我第一时间写下《阅读蒋敏德》。文章发表后,引起巨大反响,却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—— 不少不明情况的人跑到未来食品厂索要捐款,给企业造成诸多困扰。受企业所托,我连夜撰写《莫把蒋敏德当做“唐僧肉”》。当那些索要捐款的人在未来食品厂办公室看到摊放的报纸文章时,只能悻悻离去。听闻此事解决,我也松了口气。虽与蒋敏德素未谋面,但因文字结缘,他十分欣赏我的文章,后来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,他甚至会跟我分享儿时的生活细节,想来,这都是《富阳日报》搭建的奇妙缘分。
报社似乎总是在搬迁。当我得知《富阳日报》迁至花坞南路原电视台旧址时,我已许久未曾投稿。某天,我意外地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散文《牵着丝瓜的手跟我回家》。这篇一年前用方格稿纸手写的稿件,投稿后一直没有回音,我原以为早已石沉大海,没想到时隔许久,竟以一种充满仪式感的方式发表,也让我记住了新任副刊编辑蒋立波的名字。直到有一天,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,正是蒋立波打来的。他从姚总编那里拿到我的号码,真诚地邀请我为报纸的专栏供稿。面对如此诚意满满的约稿,我当即答应下来。此后,一篇篇话题文章接连在报纸上发表。
在给《富阳报》写文章的日子里,我时常觉得像是在给朋友写信,字里行间都是真诚与热爱。自蒋立波担任副刊编辑后,我的写作热情被充分点燃。在副刊和话题专栏的创作中,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作者,大家常常聚在一起,热烈地探讨如何写好民生话题文章。生活中的话题无穷无尽,然而专栏的兴衰自有周期。如今,报纸上的话题专栏已不复存在,我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后来,报社又迁至位于体育馆路的文创大厦,我去过几次,那里气派非凡,颇有大报馆的模样。特别感谢那段时光,报纸为我开设了“老夏春秋”专栏,让我那些略显粗糙的小文得以连续刊登近半年。后来,报社还以“记忆看见我”为题,举办了“老夏春秋作品研讨会”,这份情谊,我永生难忘。这便是报纸的魅力,它如一座桥梁,紧密地连接着读者与作者。
在海正药业工作时,我常因工作需要前往富阳区文化中心。当有一天,在文化中心,我意外遇见许多老熟人,才发现原来报纸与广电合并了。
尽管纸媒衰微,但“桃花依旧笑春风”,我内心那份对家乡媒体的热爱与支持,永远不会改变。